 上海博物馆的战国楚竹书使用了楚国特有的地方文字。 (图片来源:浙江慈溪图书馆) |
《左传》与《国语》所记载的筮例是研究《周易》相当珍贵的资料,让我们可藉以了解春秋时代史官与卜官如何解卦,并藉以建构出专属于《周易》的占断方法。
这些与《周易》相关的记载共有二十二例,但是真正的筮例只有十七则,其余则只是引述《周易》,并不能算是筮例。 这些记载中却有两则所引述的《周易》与今本经文不一样:
- 《左传》秦穆公筮伐晋:得蛊卦
卜徒父曰:「吉,涉河,侯车败」; 「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
《周易》:蛊,元亨,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 《左传》晋厉公筮鄢陵之战:得复卦
晋史曰:南国䠞,射其元王,中厥目。
今本《周易》:亨。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些差异? 推论有以下几种可能:
- 千年传抄的误差。
- 史官和卜官信口开河,引错了!
- 此为商朝所传的归藏易。
- 周易还在发展之中。
这四种可能都有其道理,没有那一个比较正确的问题。 或许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出土的考古证据提供更确切的答案,在此之前,没必要争得面红耳赤,认为此是彼非。
同时,也很有可最后答案是一个复选题。 例如,可能是周易的确还在发展而未定,但其中也存有传抄之误差。 或者这是商朝的筮书,但引述还是有些误差….。
但这些可能中,以第四项是最具启发性与突破性。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左传》的这些筮例就是《周易》发展与成书过程的记录。
以下我们分项探讨这四种不同的可能。
千年传抄的误差
对任何古书来说这都算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需什么特别的论证,因为传抄过程中的可能人为错误本就是非常自然而极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因此这个看来简单直觉而不需什么验证的答案,却真的是非常有可能的。 只是,自古似乎没人这么怀疑过。
这是因为,这是一本「圣经」,自古就没人敢怀疑做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经中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圣人之言,都是不容有任何更动的金科玉律,怎么可能会有错误! 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与枷锁下,自汉以来,没有一个读书人可以怀疑经文自始就不是那个样子。
但试想,《周易》这本书从周至汉初近千年的时间里,历经数百年战乱与秦火,又不知辗转经过多少手的传抄,传抄过程不知是有拿着另一竹简在旁朗诵还是只是以不可靠的记忆背诵出来,当中还面临了语文及文化的差异。 因为秦时才统一文字,既使文字真统一了还有方言不同的影响。 像楚竹简就可清楚看出地方语文影响有如何巨大,许多经文都是以楚国特有的文字在书写。
所以从第一手的《周易》到后来我们现在见到的《周易》,可想见的,一定存在很多谨误,很多地方与第一手《周易》(如果有的话)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就算有断简残编也不需意外。 这个理所当然的重大问题,只差我们没有可靠的古本来做校订而已。
事实上,比对现代出土的《周易》古本,例如马王堆的帛书《周易》(大约抄写于汉文帝初期,可参考谈易经的卦序与卦名问题–从帛书本谈起),还有上海博物馆的战国楚竹书,不要说在经文上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连最简单而基础的卦名都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对于《左传》引用的《周易》经文与今本不一样,或许不需过度解读,很可能就是很单纯的千年传抄的误差–就这么简单,没了!
那么,《左传》所载,或许才是更接近一手《周易》的原文。
杜预:史官和卜官信口开河
在“秦穆公筮伐晋”筮例中,杜预注说:
徒父,秦之掌龟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据其所见杂占而言之。
又说:
今此所言,盖卜筮书杂辞,以狐蛊为君,其义欲以喻晋惠公,其象未闻。
杜预意思大概是说,徒父是秦国的卜官,掌管的是龟卜,对于如何占断筮卦,他不是很懂,三易(指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周之周易)他不能融会贯通,所以就随口乱说。 以狐蛊来比喻晋惠公这样的取象,也是没听说过的,言下之意似指徒父是在瞎掰。
杜预这样的判断,只是基于他对卜徒父所言的个人见解,而不是有什么具体之依据。 而说卜官不懂筮法的占断更是武断,我们观全部春秋筮例,对于《周易》的使用,有两种人堪称专家:一是史官,一是卜官。 一些王公贵族自己筮卦之后有不懂的,也都是请教卜官或史官。
又《周礼》记载:「大卜掌《三兆》之法,… 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周礼》中三易既是太卜所掌管,在诸侯国中应当也不例外,这也是为何春秋筮例经常由卜官出来解卦做最重要的占断。 如果卜官不是专家,什么才是专家?
「晋厉公筮鄢陵之战」筮例中晋史所说「南国䠞,射其元王,中厥目」,杜预则注说:
此卜者辞也。 复,阳长之卦,阳气起子,南行推阴,故曰南国䠞也。 南国势䠞,则离受其咎,离为诸侯,又为目,阳气激南,飞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杜预说这是「卜者辞」相当奇怪,因为《左传》明明说「公筮之」,「其卦遇复」,怎麽会是「卜者辞」? 但个人猜想,杜预想表达的有点是前一筮例的意思,就是他认为晋史引错了,所引述根本就不是周易,类似于前面所说的「筮书杂辞」的意思。 或者是,这就像卜人一样,随口而即性之创作,不是真的引述周易。
简单说:杜预认为这两个筮例之所以出现与今本《周易》不一样的经文,是史官或卜官不专业,引错了; 或者只是他们的即性创作。
我们观《左传》的前后文,由于并未明指《周易》,只是简单的在「其卦遇x」之后用一「曰」字,那麽杜预的说法,虽然他说卜官史官不专业实在过于武断,但的确有可能卜官与史官并不是真的在引述《周易》,而只是随口说说,或是这两个筮例中刚好他们引错了。
话又说回来,杜预之所以做这样的判断,大概也是在以《周易》为圣经,不可能有错的立场上,假设杜预是现代人,没了圣人之言的这种思想禁锢,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连山归藏易
杜预注显然认为那些并不是连山或归藏易,但这与后世多数学者见解并不一样。 如顾炎武《日知录. 卷一》论“三易”说:
《左传》僖十五年,战于韩,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 成十六年战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䠞,射其元王,中厥目。」 此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 (卜徒父以卜人而掌此,犹周官之大卜。 )而传不言易。
顾炎武直接以所引占辞与今本周易不同而判定这些都是《周易》之外的三易之法。 所谓三易是指夏朝的连山,商朝的归藏,以及周朝的周易。 换句话说,亭林先生认为这就是连山易或归藏易的占辞。
这样的见解长期以来一直为诸多学者所支持,几成定见,就算像高亨如此不执于传统而勇与突破的现代学者,也理所当然的接受这个主张。 《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中就评卜徒父说:「很明显的是卦辞,但不见于周易,当是出于周易同类的筮书,如连山、归藏等。」
「三易」之说源自于《周礼. 春官. 太卜》: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 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 其经运十,其别九十。 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氐高作龟。 大祭祀,则氐高命龟。 凡小事,莅卜。
又说:
占人掌占龟,以八簭占八颂,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凡卜簭,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凡卜簭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 凡国之大事,先簭而后卜。 [按:簭即筮; 眡即视。
连山与归藏易两书的存在与否,至今仍是一个无以证实的事。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收有连山一卷、归藏一卷,而当代王家台出土秦简许多地方还可与马国翰所收者相印证,因此被视为就是《归藏》易。 然而,有学者考证认为这归藏极可能成书于战国时代,晚于《周易》。
张政烺的数字卦研究发现中,目前可考的六画数字卦可溯源自商初,那么现今《周易》所用的六画卦占筮方法也应当至少推至殷商而非周朝。
所以,商朝甚至夏朝时就存与类似于《周易》的筮书完全不足为奇,只是是否真的名为《连山》和《归藏》则有待商榷,或许有别的名字,或许真的叫连山、归藏。 但无论如何,今传的归藏比较可能只是战国之后之伪作,也有可能只是战国时另一套与商朝筮法无关的筮书。 《礼记》孔子曰:「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这与传说中《归藏易》以坤为首的说法亦相符,也有学者认为这《坤乾》就是归藏易,但其内容完全失传。
由此看来,所谓的文王演周易或许讲的只是文王改造殷商之筮书为适于周朝信仰的筮书。
张政烺考证就发现,现今《周易》使用的「九」数,是在西周之后才出现,而六、七、八、九四个筮数定下来也大概是这个时候。 而在此之前,数字卦从一最多只用到八,可清楚看出以「八」为极数之信仰框架。 我们单从今本《周易》就可看出许多对于八这个数字的崇拜,如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春秋筮例中唯一被引用过的占数就只有八,八共被引用三次,但未见六、七、九三数字被引用; 《周礼》还说太卜「以八簭占八颂,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簭即筮; 眡即视)。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现今《周易》对于「九」的崇拜,应是周朝建立之后以商朝版本的周易(可能叫《归藏》或《坤乾》或《易繇阴阳卦》或其他什么的)所改造而来,「八」数的崇拜部份是属商朝所遗留下来的,而属九的信仰部份,则是周朝所改造加进去的。 这个假设与数字卦的发展可互为印证。
只是,商朝的筮书与今本周朝筮书到底差别多大? 完全无从推敲了,因为目前为止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本可考的商朝筮书。 更何况今本之周朝筮书到底何时成为今天之面貌,也是一个大问题。 就算有商朝筮书,春秋时商朝都已亡数百年了,有周朝的筮书为何还要引用商朝的? 这个道理也是讲不通的。 而如果史官或卜官要引用较少用的筮书,理应会引用书名才是。
我们再回到《左传》这两段记载,比对世传的所谓「归藏易」,完全是不一样的文风,但这并不具任何意义,最终这个问题还是两边都落入了无解的迷团。
但总而言之,在四种推论中,这个最历久而主流的见解,个人认为却反而是最不可能的。
发展中的《周易》
很可能《左传》这些记载,正是《周易》在春秋时代还在发展之中的证据。
关于周易如何成书这个问题自古一直分成两大派:一派认为是一人一时之作,至于是何人? 这个人就不见得是周文王了。 另一派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
我的看法坚决认为是后者。 「三易」之说虽不尽然完全可信,特别是商朝或更早之前的筮书是不是叫归藏或连山更是相当值得怀疑,但今存周易早在周朝之前就另有底本,却是可从各种资料来相互印证的,例如数字卦之研究已确定类似于《周易》的筮法真的在商朝就有。
其次依《周礼. 春官. 太卜》所载或可推敲出卜筮书如何形成。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郑玄注说:「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 颂,谓繇也,每体十繇“。
《左传》孔颖达疏则说:「然则卜人所占之语,古人谓之为繇,其辞视兆而作,出于临时之占,或是旧辞,或是新造,犹如筮者引《周易》,或别造辞。 卜之繇辞,未必皆在其颂千有二百之中也。」
据孔疏说法,卜法中的「繇」(颂),可能是取用既有的记载(类似于筮法中的《周易》爻辞),也有可能是新作。 所以,卜人在解兆象时会有些吉凶法则可供占验,而解兆者可能取用旧的、先人所造,既有的颂辞,但也会加入自己的即时创作。 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筮法的占断上。
我们从春秋一些卜筮相关记载中也可看到,卜官或史官在解龟卜兆象或是筮法卦象时,有许多的自我发挥的即时创作,例如在「田氏代齐」故事中,田完在齐国时,国懿仲要将女儿嫁给田完,问了卜,结果说:
凤皇于飞,和鸣锵锵; 有妫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这很显然的是即时之创作,而非以既有的颂辞做占断。 因为内容都是直接清楚而具体的回答了所问之事情,但也很可能借用了一些既有的占辞,或者有一种类似「公式」的创作法,根据实际情况而加以套用。 例如「xx于飞」就是在古代相当常见的语法,可能吉兆就会用「凤皇于飞」,凶象就改用「明夷于飞」等等的。
我们到一些中国的风景区去旅游时,有些以姓名帮忙游客实时作诗的商品,多少也是利用类似的创作法。 他们使用一些既有的公式,拿到游客名字之后套进公式中即可。
在筮法中,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筮例中,史苏如此解卦:
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 女承筐,亦无贶也。 西邻责言,不可偿也。」 归妹之睽,犹无相也。 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 为嬴败姬,车说其轿,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 归妹睽孤,寇张之弧,姪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 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
史苏的解卦方式,也是出口成章,以诗歌方式表达,里面许多的即时创作,若混入卦爻辞大概也很难被挑出。
当然的,史官或卜官在自我发挥时,应当是有些判断吉凶的法则的。 就如我们在《左传》筮例中看到的,经常是从八卦的卦象去找灵感,同时他们还有些常用的技巧,如互体、爻变、贞悔等等的。 但卦象、灵感、与事情最后应验之间的连结,并不是一个科学而逻辑的因果关系,但古代则是透过统计与整理数据库的方法来强化与修整这种关联。
这也就是《周礼. 春官. 太卜》所说的:「占人掌占龟,以八簭占八颂,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凡卜簭,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凡卜簭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簭即筮)
「占」字从卜从口,就是把龟卜的兆象解读出来的意思。 在筮法上,「占」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解卦」,把卦象解读成常规人可以了解的语言。 而「占人」主要掌管的是与卜筮占验相关的事,包括视吉凶(眡即视之古文),同时还要在卜筮结束之后,整理资料归档,在每年结束的时候做占验与否的整理统计。 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归档整理,应当会做为未来占断的参考之用,最可能的运用方式,就是拿来维持一个占断参考的数据库,这或许就是卜筮书的成书基础,或者,这才是真正的《周易》–真正的周易,其实是一个由占人所维护的活数据库,它是年年依最新资料做增删与修订而有新版!
换句话说,《周易》这本筮书可能是一个由国家机构所掌管维护的一个活的数据库,年年修订,年年不一样,并不是死的,一成既成的。
由此反推,那么所谓的商朝的「归藏」,可能只是这套「活的数据库」在商朝结束之后的一个总归档。 「归藏」或许只是将商朝的筮书「归档而藏之」的总结意思,就是将商朝的筮书资料库发展画下一个句号,随着它的时代结束而整理放到国家档案库中。 而所谓周文王演周易,很可能只是在「归藏」的基础上,重建并继续发展属于周的新的数据库。
至于到几时,什么情况下,周朝的这个活的资料库才变成了一本死书– 也就是内容不再更新,不再修订、发展的一本书,而成为今本的《周易》样貌? 比较可能是与周室之兴衰连动的。
在东周的春秋时代《周易》传入诸侯国时,或许《周易》这个数据库一方面还未死(另一说法就是还未定下来),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更新较少而已经发展成与今本很像了–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可能还有年年在更新,但随着周室之衰微,其更新已不若过去。 所以一方面,我们见到《左传》所载多数还是与今本《周易》完全一样,另一方面也见到少部份卜官或史官所引用《周易》与今本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我们再回头看卜徒父所说的「吉,涉河,侯车败」与「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虽说与今本蛊卦卦辞不一样,但也有些相像且可相贯通之处,例如前半段和今本「蛊元亨,利涉大川」很相似,只差没有「侯车败」一句。 而后半段连两句都有「三」字,「千乘三去,三去之余」,和今本《周易》经文「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也有些微的相似,这卦可能是历经较小修改的范例。
而晋史所引复卦的「南国䠞,射其元王,中厥目」则与今本几乎完全不一样,这可能是历经了更大的增删的范例。
如果我们把《周易》当做是一个由国家机构在掌管、维护,与更新的一个活数据库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死书」来看,那麽周室衰微诸侯群起的春秋时代正好是《周易》处于最后演进与形成定本的时候,那么这些差异不但非常合理,而且也正可做为周易演化的重要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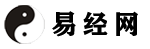













![13. 同人之第十三-焦氏易林[四库全书版]](https://www.eee-learning.com/image/yi13b.png?x-oss-process=image/resize,m_fill,h_63,w_100)



还没有评论呢,快来抢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