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举《左传》二例以观古人之占。《左传•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不指其事,泛卜吉凶,。遇《坤》匪之《比》圍(《比》,《坤》六五爻变),曰:‘黄裳元吉。’(《坤》六五爻辞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坎》险,故强;《坤》,故温。强而能温,所以为忠);和以率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黄);下不共,不得其饰(不为裳);事不善,不得其极(失中德)。’外内倡和为忠(不相违也),率事以信为共(率犹行也),供养三德为善(三德,谓正直、刚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当(非忠、信、善,不当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夫《易》”犹“此《易》”,谓“黄裳元吉”之卦,问其何事,欲令从下之饰)中美能黄,上美为兀,下美则裳,参成可篮(参美尽备,吉可如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有阙”,谓不参成)”
南蒯将叛,筮得“黄裳元吉”以为大吉,而惠伯结合贞问者的具体情况,认为“黄裳元吉”是中和之美,不能用于占凶险之事;且黄裳又是美饰,亦不能用于凶险之事。故而认为南蒯不能当此爻辞。惠伯之占否定了南蒯“大吉”之占,实以此反对南蒯欲叛之心。
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坎》为中男,故曰“夫”,变而为《巽》,故曰“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风能陨落物者,变而陨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六三爻辞)‘困于石’,往不济也(《坎》为险、为水,水之险者,石不可以动也)。
‘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坎》为险,《兑》为泽,泽之生物而险者蒺藜,恃之则伤)。‘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据而据,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妻其可得见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无应,则丧其妻,失其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今按:《困》之《大过》,《困》卦六三爻变,故陈文子即依《困》卦六三爻辞占之,以为凶。其实即使以变卦《大过》九三爻辞“栋桡,凶”来占,也还是凶。而众史之皆曰“吉”者,无非欲讨好崔武子。当然一定要讨好,理由也找得出,即《困》卦卦辞有“亨,贞,大人吉,无咎”,引用一下也是很方便的。而崔武子本人更是出了奇兵,认为棠姜是个寡妇,一切凶象都巳应在她的前夫身上,坚持娶了棠姜。
由《左传》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想起《周易古篮考》记载的关于《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的轶闻:纪昀年青时应乡举,老师为他卜卦,筮得《困》之六三,即“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师以此卦为不吉,纪却说:“吾尚未娶,何妻之可见!‘不见其妻’者,莫之与偶也,恐中解元耳。
‘困于石’者,或第二名姓名有石字,或石旁也。”据说发榜之后,纪昀果然位居第一,第二名则石姓也。而更有奇者,第三名姓米,盖因“米”字字形像蒺藜的形状,故曰“据于蒺藜”也®。
不论事之真伪,纪晓岚与春秋时的崔武子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以为娶寡妇,夫的凶都已应在前夫身上;一个以为己未娶,夫的凶还应不到自己身上。这或许也可以称为理论联系实际罢。
对于相同的卦象或其所系之辞作出不同的解释,不但是正常的现象,而且还有其必然的道理。因为书上记的是以往的经验,现在面对的是眼前的事情,且目的是要预卜(预知)未来之事。既然各人有各人的“眼前”,当然“未来”也不可能全然一致。因此“占”的结果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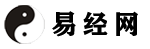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呢,快来抢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