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到底怎样看待《易》及其卜筮
据《孔子家语》和《乾凿度》等书的记载,孔子年轻时对于《易》的本质并不大理解,常为自己占筮。一次,他偶然占得‘‘贲”卦。因为“贲”的意思是文饰、文采,所以孔子觉得不中心意,于是“愀然有不平之色”。(《孔子家语》:“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愀然荀不平之色。”)有一次他偶尔占得“旅”卦,自己吃不准,便请教丁-商祺。“旅”卦卦辞为:“小亨,旅贞吉。”有象征占得此卦者虽然集大道于一身,却不能将此道广施于天卜之意。所以,商瞿对孔子说:“子有圣知(智)而无位。”意思是说先生您虽然具有圣人的智葸,却没有圣人的权位。孔子听后哭泣着说:“凤凰不飞来,黄河没有龙图出现,这真是天命啊!”(《乾凿度》:“孔子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杀知而无位。孔子泣曰:‘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天之命也。.
尽管孔子相信天命,然而他却不听信天命的摆布,依然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努力进取。这从他一生的经历可以肴出来。孔子不为幼年的家境贫困所压倒,15岁即“志于学”。他学习既是为了修德,更是为了进业。当在乡里崴得“博学”之盛名后,就径自敢于挑战“学在官府”的传统,首创私学,将自己的学业贡献于社会,促进学术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和普及。为了更好地实现济世的理想,孔子积极寻求入仕,并在担任中都宰和大司寇以及摄行相事的短暂时间里,大显身手,尔后虽然屡遭挫折,俱仍然矢志不渝,在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中,其所费的心力和所遭受的艰辛,就足以证明这一点。ft到暮年,尽管入仕的志向最终未能遂愿,但他仍痴迷于自己所酷爱的教俘和文化典籍的整理。
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仅有这样的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韦”,指熟牛皮条。古代用竹片写书,再用牛皮条编缀成册;“三”,泛指多;“绝”,即断。怠思是说,孔子晚年專欢读《易》,撰写了《彖》、《系辞》、《象》、《说卦》、《文言》。反复读《易》,致使编缀的皮条多次断开。他(感慨地)说:“如果多给我几年功夫,那么,我对于《易》所蕴含的礼仪则更加理解了。”
从司马迁的这段文字,我们至少可以领会这样三个问题:
一是孔子晚年喜欢《易》,喜欢到因反复翻读,致使编缀《易》的皮条多次断开的程度。
二是孔子把读《易》的心得记载下来,编写了《彖》、《系》、《象》、《说卦》、《文言》等传,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易大传》。
三是孔子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读《易》,以至于感慨地说:“要是多给我几年功夫,那么,我对于《易》所蕴含的礼仪就会更加理解了。”
只此三点,不仅足以说明了孔子对于《易》的喜爱程度,而且说明了孔子与《彖》、《系》、《象》、《说卦》、《文言》等通常所说的《易大传》的关系。
但是,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述不洋,相关史料和文献的缺乏,以及人们的理解又见仁见智,致使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历来分歧和争议颇大。
—、到底孔子“晚”到何时才喜《易》,以至于“读《易》,韦编三绝”?
二、到底孔子对于《易》的整体认识以及占筮的态度如何?
三、到底孔子与《易大传》是怎样的关系?他在《易大传》的创作上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我现在就这三个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孔子到底“晚”到何时才喜《易》呢?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没有明确说明,而历代人们对此也说法不一。从总体上说,历来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孔子是在50岁之时,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在50岁之后。而在认为孔子50岁之后喜《易》的意见中,则又分为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是在60岁之前,而另一种则认为是在60岁之后。
从《左传》、《国语》看,其中关于用《易》占卜论事的记载就有二十多条,学习、应用《易》的人广泛地分布在周、鲁、卫、郑、晋、齐、秦诸国,说明当时《易》已经广泛流传。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十有五而志于学”,博览群书且不到30岁就收徒讲学的孔子,在接触其他历史文献的同时,自然不会不接触《易》。
从相关的史料和文献看,孔子对于《易》的理解,同学习的一般规律一样,历经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不知“本”到知“本”的过程。由于史料和文献的不洋,我们虽然不能确知孔子在学《易》方面所历经的、具体年龄段的变化,但也可以作出大体的推断。
从《孔子家语》所id载的孔子“常&筑”,而卜得“贲”卦,“愀然有不平之色”,以及卜得“旅”卦而请教他人来看,孔子起初确实“不知《易》”,即不了解《易》的本质,一度相信占筮。这可能发生在他自白的“不惑”之年即40岁之前。
而从《论语》的相关记载看,在周游列国期间(55~68岁),孔子已经逐渐熟悉《易》,认识了《易》的本质,并对其中的一些卦格外重视。例如,从马王堆帛书《易》、《缪和》的记载看,孔子对“困”卦就格外重视。该篇记载说,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英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尤之。是故汤□□王,文王拘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贱困于(会稽),晋文君凼(于)骊氏。古古至今,柏天之君,未尝困而能……也乎?困之□为达也,亦猷……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此)之谓也。”对于帛书《缪和》中的“子曰”,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将该篇与相关文献如《庄子•杂篇•让王》、《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和《说苑•杂言》等联系起来看,便不难断定这里的“子H”无疑就是指“孔子说”。其中尤以刘向在《说苑•杂言》中的记载较详:
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由,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知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终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乐不休,子路愠见曰:“夫子之修乐,时乎?”孔子不应,乐终而曰:“由,昔者齐桓霸心生于莒,勾践簕心生于会稽,晋文簕心生于骊氏,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锊不广,庸知而不遇之。”于是兴,明u免于厄。子贡执巒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恶是何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其大意是:孔子在陈、蔡之境逍难,没有了粮食吃,弟子们的脸上都露出饥色,可孔子依然在屋里歌唱。子路进去问:“老师您这样唱歌,合乎礼吗?”孔子不回答,等唱完一曲才说:“子由啊,君子喜好歌乐,并无骄横之意;小人喜好歌乐,却只是为了壮胆逞能,这道理谁知道啊?你是不理解我才跟随我吗?”子路不髙兴,拿起盾牌起舞,舞了三回而出来。直到第七天,孔子仍修乐不止,子路气呼呼地见孔子说:“老师您这样修乐,合乎时宜吗?”孔+不回答,等歌唱完了才说:“子由啊,以前齐桓公的称筋之心就萌生在莒受困之日,勾践的称霸之心就萌生在会稽受辱之时,晋文公的称霸之心则萌生丁•骊氏逍难之际。所以,居处无忧,则思考不会深远;身不受困则志向不会广大,智力低下的人不会有这样的遭遇的。”于是大家高兴起来,到次H困难过去。子贡牵着溜绳说:“咱们几个学生跟随老师遭遇此难,可不能忘啊!”孔子说:“倒霉算什么?古语难道没说吗?三次骨折成了良医。在陈、蔡之间受困,是我孔丘之幸运啊!你们这两三个学生跟随我一起受困,都是幸运之人啊!我听说人君不受困就不能成王,壮士不受困就不能前进。从前成汤受困于吕,文王受困于羑里,秦穆公受困于殽山,齐桓公受困于长勺,勾践受困于会稽,晋文公受困于骗氏。说起受困之道理,如同由寒转暖,由暖转寒而已,惟有贤明的人才独自知晓其屮的道理而不便明说啊!就如同《易》所说的:‘处丁•困境而仍能坚守其贞德即亨通其道的人,则仍然吉祥。所以说‘大人吉,无咎。在受困之际,光凭嘴说,人们不信,关键的是怎么去做。所以,圣人与一般人所讲的信用,是不一样的。”
将帛书《易》之《缪和》、竹简《穷达以时》以及刘向《说苑•杂言》等文献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对照,则不难发现他们的论述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用缪和的话说,人之生于天下,都希望“利达显荣”,但孔子认为“人君不困不成王”,所以,“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面对所遭遇的困境,就像是面对寒来暑往一样自然,惟有信守正道的人独自心中有数而不便言明。
孔子为什么格外重视《易》中的“困”卦?大概与他个人的阅历和感悟有关。他满腹经纶,踌躇满志,但在仕途上却屡遭坎坷,壮志难酬。“而立之年”想在自己的祖国入仕,却因“三桓”肆虐而不得志,避难齐国虽然得到齐景公的赏识,却未能见用,不得不回到鲁国,但因“陪臣执国政”,“离于正道”的政局依然未变,故打消入仕的念头,“退而修《诗》《书》《礼》《乐》”。好不容易熬得乌云暂退而执政五年,政绩卓然,“四方则之”,却终因奸邪挡道而不得不祈求到列国发展。然而,尽管他四处奔波,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叶之间,磨破嘴皮,到处游说,却知音难觅,响应者寥寥,而且处处碰壁,屡屡遭难,以至一连几天连肚皮也填不饱,陷人“累累如丧家之狗”之窘境,就连跟随的弟子们也一度怀疑、抱怨。正是在这样的人生磨砺中,孔子逐渐揣摩、领会了《易》,尤其是“困”卦的本质。而帛书《易》、《缪和》所谈论的“困”、“达”问题,不仅表明了孔子当时所处的窘况,而且也表明了孔子当时对于《易》的认识,及由此所领悟的人生境界,都巳经达到新的髙度。
孔子逍遇陈蔡之困,发生在兽哀公四年。这时孔子61岁,刚过他所自诩的“耳顺之年”。他借当时的处境现身说法,阐发《易》的人生真滞,表明他当时对于《易》的研究和体悟,已经相当深刻了。
再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的记载看,孔子晚年对于《易》的喜爱可以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帛书《要》关于孔子和子贡的对话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勿(于)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翟(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
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徳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在解释这段文字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巫史”这两个字的涵义。
“巫”和“史”其实是古代两种不同的专职人员。“巫”,在远古是沟通天地、神灵、祖先与人之间联系的专职人员,掌管祭祀、卜筮、星历、驱邪、治病等事;而“史”则是从巫中分化出来的,旨在掌管天文、历法、卜筮、历史等的政府工作人员。因此,“史”是在国家、政府产生之后才出现的先有“巫”,而后有“史”。“史”仅存在于政府之中,是政府中的一^职位;而“巫”则广泛存在于全社会;“史”、“巫”在职能上虽有相同之处,例如都从事卜筮活动,但具体目的却不一样。
在了解了“巫史”的涵义后,我们可以解释这段话的大意了。其大意是:
孔子老了而喜好《易》,待在屋里时把它放在身边的席子上,出行时就把它放在行囊之中。学生子赣问他:“老师您当年教我们这些学生时说:‘缺乏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我相信您的话,并且照您的话去做。可老师您怎么老了却也喜好这玩意儿了?”
孔子说:“君子说话向来是讲究准则的。剪除凶怪以求得吉祥,祓除灾殃以求得福祉。察看其要点,违背其德。《尚书》多有忽视,而《周易》则未曾丢失,而且里面还有古人的遗训。我并不一味地去卜筮。”……(子赣说:)“我听好多老师说:遵循正道而行仁义,那就不受困惑。可老师您现在不喜好《易》的卜筮之用,却喜好读它的卦爻辞,这是存心在常人面前标新立异,是奇邪不正的做法,(怎么)可以呢?”孔子说:“错啦!子贡!我来告诉你。《易》的道理……所以《易》的道理,使阳刚知道恐惧,使阴柔知道刚强;使愚笨的人做亊不妄为,使(聪明的)人做事不欺诈。周文王仁义,因为不得志才忧国忧民a而纣王无道,倒使得文王有所作为。为了避讳和招惹灾危而推演八卦,这样才使得《易》开始兴旺起来。我喜欢其钾惹……”子赣问:“老师您也相信其卜筮吗?”孔子说:“我占一页次而有七十次准确,就是周粱(梁)山之占法,也必然依照占得的多数相同的结果来断卦啊!”孔子说:“对于《易》,我把占问吉凶看作是次要的,我所®要的是探明卦象之徳义。学易的人应该通过卜筮沟通神明和人,以赞助造化神明的德行,从而明了数的神妙义理,再通过明了数的神妙义理进而明了卦象的德义。这样,在依据卜筮的结论作决断时,自觉地做到服从卦象的德义,内心恪守于仁^行为适合于义。如果通过卜筮只会沟通神人以赞助造化神明的德行,而不能明了数的义理,那就成了“巫”;而通晓了数的义理却乂不能明了数的德义,那也只不过是“史”。“史巫”的卜筮之术,我虽叫往它,却未呰去追求;我虽然苒欢它,但内心却不以为然。后丨tt的人如果要怀疑我孔丘的话,可能就是在《易》上。不过,我只是探索卦象的徳性,我与“史巫”是“同途殊归”(我们虽然都讲卜筮,但我要的是卦象的德性,而“史巫”要的则是卜筮的吉m0君子靠德行以求得福祉,因而虽讲祭祀,但并不频繁地举行祭祀活动;靠信守仁义以求得吉祥,因而里讲卜筮却很少应用。祝巫们靠卜筮以求吉凶的做法,对于君子来说是次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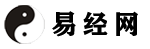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呢,快来抢沙发~